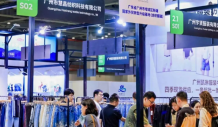2卡地亞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基金會首次在中國舉辦的展覽《陌生風(fēng)景》正式向公眾開放,位于上海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博物館5至7層,將持續(xù)至8日。該基金會由法國奢侈珠寶品牌卡地亞(Cartier)1984年創(chuàng)立,與品牌的主營業(yè)務(wù)并無太大關(guān)系,而是專門支持和推廣知名、亦或未成名的藝術(shù)家作品,目前已收藏了350余位藝術(shù)家的1500個作品。此次參展的藝術(shù)家有31位,帶來了100多個作品。
在《陌生風(fēng)景》中,數(shù)字化、科技化設(shè)施和沉浸式體驗的展品數(shù)量較多,對于大眾來說,更容易領(lǐng)會藝術(shù)家想要表達(dá)的思想,也增添了更豐富的體驗。我們在《陌生風(fēng)景》的百余個作品中找到了一些有趣的展品重點來說一說。
集導(dǎo)演、作家和畫家為一身的北野武帶來了畫作和裝置藝術(shù)。在博物館5層,展覽著他的畫作系列《畫家的孩子》和動物和花卉形象的花瓶。他曾在2010年就和卡地亞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基金會合作展出了《畫畫的家伙》,那是他首次以畫家的身份面世。北野武的電影雖然常有暴力和憂郁的色彩,但他在畫畫時好像翻出了內(nèi)心童真而多彩的一面。在展廳一樓,還有他創(chuàng)作的大型裝置作品《北野縫紉機“秀吉”》。該裝置由紙板、金屬、布和泡沫板制成,上面涂著顏料,色彩和畫作一樣濃郁而鮮亮。
在5層的西北角,有兩座巨大的人像雕塑作品《購物的女人》和《在床上》,出自澳大利亞藝術(shù)家RonMueck之手。他的雕塑以混合媒材為主,突出寫實主義,會讓人覺得有趣,也會讓人心生恐懼。因為他的作品有時非常龐大,而有時是比正常比例矮小許多,從來不是正常的人體尺寸。此次參展的作品就是前者,無論是血管、皺紋、發(fā)絲,甚至是痣,都能看的一清二楚。可能是因為慢工出細(xì)活,他的創(chuàng)作速度較慢,目前雕塑類作品不到40件。
同在5層還有一個名為《動物大樂團》的展廳,看名字好像十分童趣,但這確實一個嚴(yán)肅的藝術(shù)項目。美國藝術(shù)家BernieKrause原是一位音樂家,他用了40年時間收錄了近5000個小時來自陸地和海洋自然之聲,其中包含近1.5萬種動物的聲音。他踏過了許多氣候和環(huán)境不同的地域,因此這些聲音也能體現(xiàn)不同地區(qū)的生態(tài)多樣性。同時,也提醒著人們這幾十年間生物多樣性大幅下降的狀況。
為了更有美學(xué)地展示這些聲音,創(chuàng)立于英國的聯(lián)合視覺藝術(shù)家協(xié)會為Krause只做了一種轉(zhuǎn)換設(shè)備,通過音畫同步的方式呈現(xiàn)視覺效果,在展廳內(nèi)部的墻面上以聲波的形式體現(xiàn)。不同地域的背景音之間還會穿插播放Berniekrause講述的研究方法,觀展者置身其中就好像是去到了世界不同的地方。
博物館7樓的展廳中,蔡國強的作品占據(jù)了很大一塊面積。此次他展出了三件作品,一個是配合《動物大樂團》而做的巖穴壁畫《白聲》,還有木質(zhì)七折屏風(fēng)《時空模糊計劃》以及《地球也有黑洞:為外星人作的計劃第十六號》。他從1980年代開始變探索用火藥制作藝術(shù)的可能性,后在藝術(shù)界為眾人所知,并逐漸擴寬爆破藝術(shù)的外緣。對于中國人來說,對他的作品最為印象深刻的應(yīng)該是非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的火焰大腳印莫屬。
同在7樓的還有一個沉浸式藝術(shù)裝置,里面的作品名為《出口》,由法國哲學(xué)家、城市理論家PaulVirilio提供理念,并有多位設(shè)計成員和事務(wù)所共同制作。一個地球從環(huán)形屏幕中從左向右緩慢移動,屏幕正中央的上方隨著地球的移動軌跡,按照全球地圖的順序更換國旗,下方則是十個其他國家的國旗,這些國家代表著移民對于當(dāng)?shù)亟?jīng)濟的貢獻(xiàn)。這是一個關(guān)于全球人口遷移的藝術(shù)裝置,反映了目前各個國家的移民遷移的趨勢和相關(guān)的社會問題。包括人口轉(zhuǎn)移、流動資金、難民遷移、上升的海平面和下沉的城市、自然災(zāi)害和瀕危語言,整個藝術(shù)裝置觀看完畢需要45分鐘時間。
與《陌生風(fēng)景》同在當(dāng)天開幕的展覽還有法國雕塑家、攝影藝術(shù)家ChristianBoltanski的《憶所》,這也是他首次在中國辦展。參展的作品中有他的經(jīng)典裝置藝術(shù)《無人之境》——是一個重達(dá)30噸、高8米的“衣山”,衣山的上方有一個紅色的機械爪。“無人”譯自法語Personnes,在法語中有“人們”和“無人”的雙重含義,Boltanski想運用這個雙關(guān)詞強調(diào)衣物所指代的“人們”最終會幻化為“無人”的情況。
把藝術(shù)的意義交給觀眾自己去體會——這種“反對釋義”的理念是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的一部分,這也是為什么人們覺得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難以理解的原因。創(chuàng)作者們?nèi)趸藗鹘y(tǒng)藝術(shù)中對于“美”的體現(xiàn),取而代之的是表達(dá)自己稍縱即逝的情緒,甚至是虛無縹緲的意向,因此對于觀看者來說有些難以捉摸,但往往也會在氛圍的烘托下提煉出一些自己的感悟。
雖然學(xué)術(shù)界尚未給出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誕生的確切時間,但目前來看,進入21世紀(jì)之后的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在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更為蓬勃。裝置藝術(shù)、新媒體藝術(shù)和交互藝術(shù)的表現(xiàn)形式越來越常見,已不止于繪畫和雕塑等傳統(tǒng)形式。